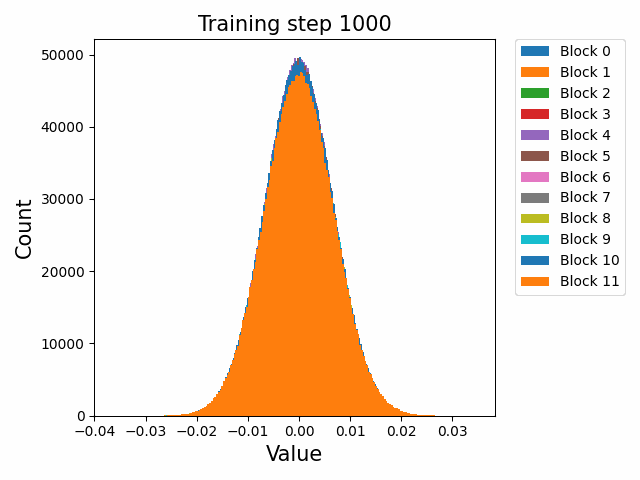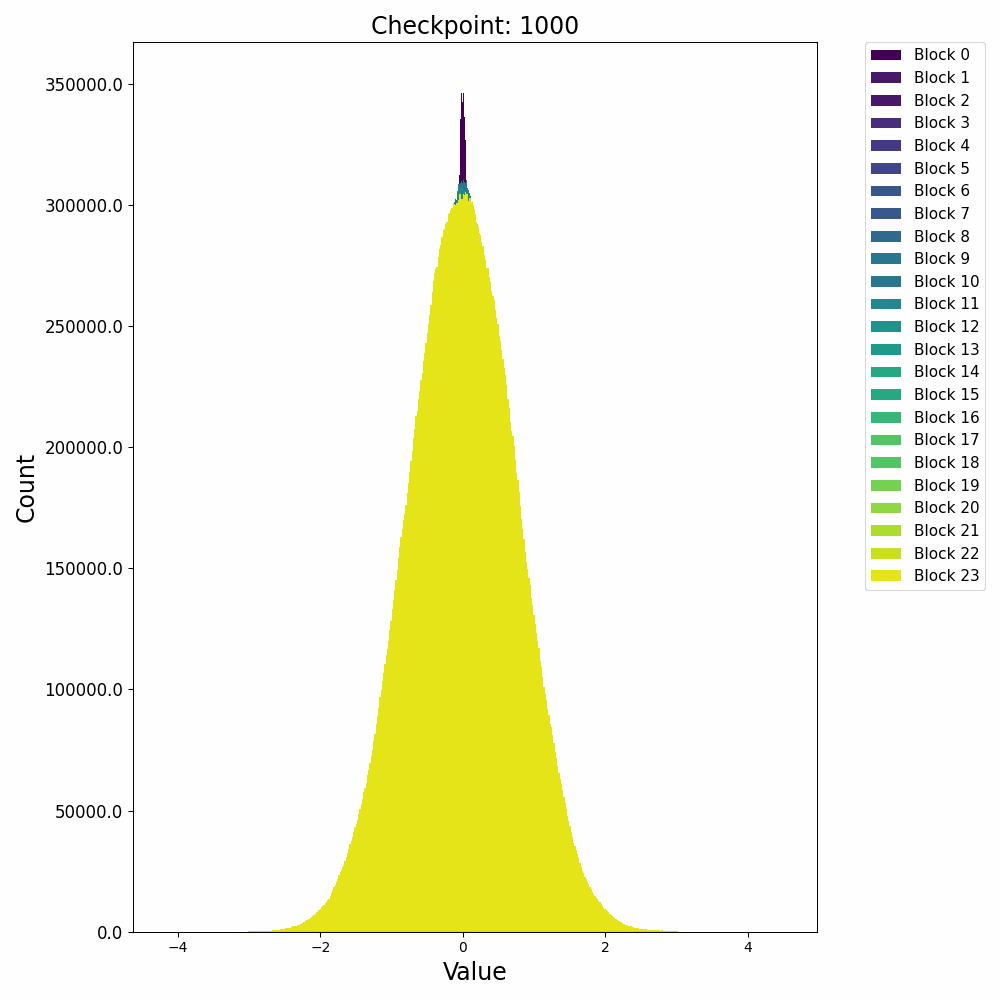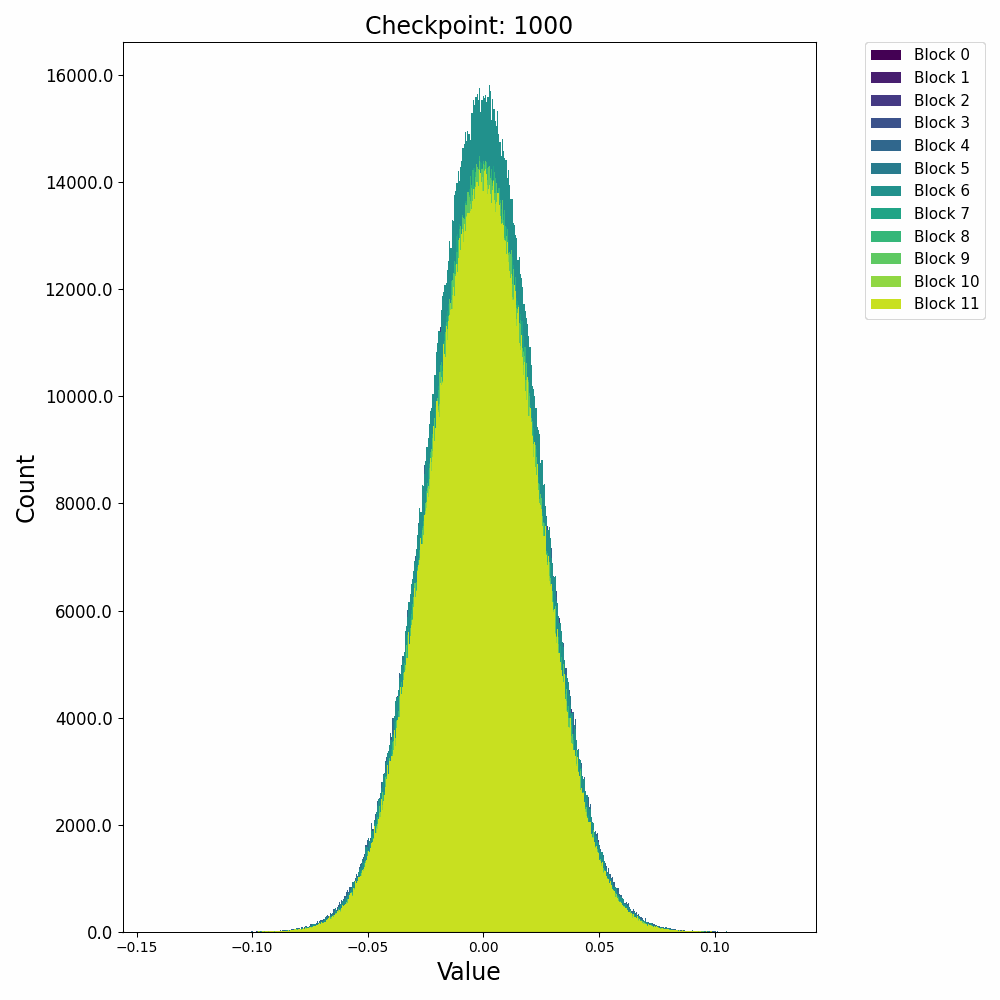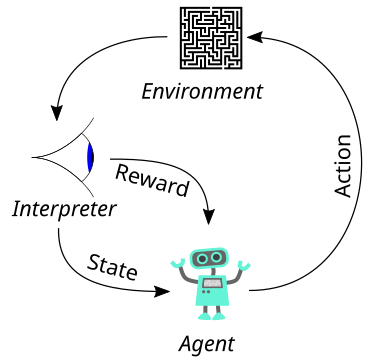在前一篇文章中,我们介绍了探针思路的设计理念,以及 Probing 分布式探针系统的整体架构。本文将详细介绍 Probing 的探针机制,包括探针的动态注入与运行时加载,以及如何规避 C/C++常见的 ABI 兼容性问题。
为何探针的动态注入能力尤为重要?因为故障和性能问题的发生总是不期而至,我们无法保证每次出现问题时都能提前部署探针。因此,任何需要提前部署的工具都迫使工程师必须”复现”问题才能进行分析,这无疑大大增加了诊断难度和时间成本。而分布式场景下,复现的成本与难度更是倍增,毕竟难以预留千卡或者万卡资源来复现问题。
异构计算则是另一个让复现问题变得更加困难的因素。在异构计算中,程序状态不再单纯地保存在 CPU 的内存中,而是同时分布在 GPU、TPU 等计算单元的内存中。这些计算设备的内存中不存在类似调用栈这种结构化数据,我们无法简单地通过 dump 调用栈来捕获故障时刻的状态,而是需要 dump 整个计算设备的内存内容。对于常见的单机八卡配置,完整 dump 一次设备内存需要占用 640GB 的存储空间,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而管理这些数据的元数据通常存储在 Python 解释器中,这意味着必须开发一个跨设备、跨语言的调试工具,才能实现完整的故障诊断。
探针则是尝试另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:
- 通过动态注入,即可实现在任意条件下调试与诊断;
- 借助探针动态操作目标进程的 Python 解释器,利用其自然可以实现跨语言、跨设备的调试能力;
探针注入的关键在于在目标进程的代码逻辑之外,额外向进程植入一段代码。常见的代码植入方式有两种:
LD_PRELOAD方法:通过LD_PRELOAD环境变量,可以让 ld.so 在加载目标进程的时候,优先加载指定的动态链接库从而实现代码植入。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简单易用,但是只能在进程启动时生效,无法在进程运行时动态注入;ptrace方法:通过ptrace系统调用,可以在进程运行时动态修改进程的内存,从而实现代码植入。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在进程运行时动态注入,但是需要对目标进程有一定的权限,且对目标进程的性能影响较大。
本文重点介绍ptrace方法的实现,LD_PRELOAD方法介绍的文章很多,本文不再赘述。
ptrace是一个 Linux 系统调用,用于监控和控制另一个进程。ptrace的调用方式如下:
#include <sys/ptrace.h>
long ptrace(enum __ptrace_request op, pid_t pid,
void *addr, void *data);
ptrace 提供了一种控制目标进程执行的方法,它可以让调试器与目标进程进行交互,从而实现调试功能。__ptrace_request 常用的取值如下:
PTRACE_ATTACH: 附加到目标进程,使其成为当前进程的 tracee;PTRACE_INTERRUPT: 暂停目标 tracee;PTRACE_CONT: 让目标进程继续执行;PTRACE_DETACH: 释放目标 tracee;PTRACE_GETREGS/PTRACE_SETREGS: 读写目标进程寄存器;PTRACE_PEEKDATA/PTRACE_POKEDATA: 读写目标进程内存,一次一个 WORD;/proc/<pid>/mem: 大块读写内存;
常见的一个 debugger 的工作流程如下:
- attach 到目标进程;
- 通过读写目标进程 TEXT 段插入断点;
- 恢复目标进程执行,并用
waitpid等待目标进程断点暂停;
- 等到目标进程暂停,通过读写内存查看信息;
这里参考了 https://github.com/Artemis21/ptrace-inject 项目,进行了一些修改。注入流程如下:
- 通过
PTRACE_ATTACH附加到目标进程;
Rust 中可以通过pete库对ptrace的封装来使用ptrace系统调用:
let mut tracer = pete::Ptracer::new();
tracer
.attach((&proc).into())
.context("failed to attach to given process")?;
log::trace!("Attached to process with PID {}", proc);
- 写入 shellcode 到目标进程的内存中;
首先找到一处合适的内存地址,具有执行权限,可以写入 shellcode。这里我们通过读取目标进程的内存映射信息,找到一个具有执行权限的内存区域:
/// Find a suitable address to inject the shellcode into.
pub(crate) fn find_executable_space(&self) -> Result<u64> {
log::trace!("Finding executable space in target process");
self.0
.maps() // 读取 /proc/<pid>/maps 文件,获取进程的内存映射信息
.context("failed to read process memory maps to find executable region")?
.into_iter()
.find(|m| m.perms.contains(process::MMPermissions::EXECUTE))
.map(|m| m.address.0)
.ok_or_else(|| {
anyhow::anyhow!("could not find an executable region in the target process")
})
}
上述代码通过读取/proc/<pid>/maps文件,获取进程的内存映射信息,找到一个具有执行权限的内存区域。接下来我们先保存这个内存区域的内容,然后写入 shellcode:
// 打开 /proc/<pid>/mem 文件,供后续读写内存使用
let mem = fs::OpenOptions::new().read(true).write(true)
.open("/proc/<pid>/mem")?;
// 根据偏移量,读取目标进程的内存
let len = mem.read_at(data, addr)?;
// 将shellcode写入目标进程的内存
let len = mem.write_at(shellcode, addr)?;
其中data是一个[u8; 1024]大小的数组,用于保存原内存区域的内容;shellcode是我们要写入的 shellcode,内容如下
/// The x64 shellcode that will be injected into the tracee.
const SHELLCODE: [u8; 6] = [
// Nop slide to make up for the fact that jumping is imprecise.
0x90, 0x90, // nop; nop
// The tracer does most of the work by putting the arguments into the
// relevant registers, and the function pointer into `r9`.
0x41, 0xff, 0xd1, // call r9
// Trap so that the tracer can set up the next call.
0xcc, // int3
];
shellcode 主要由三部分组成:
- 两个
nop指令,避免跳转时的不精确性带来问题;
- 一个
call r9指令,调用r9寄存器中的函数指针,此处调用会遵循 X86_64 下的标准调用协议,通过寄存器传参;
- 一个
int3指令,触发中断,控制流程回到 tracer;
- 通过设置寄存器调用目标函数:
在 tracer 中设置寄存器,让目标进程调用函数:
self.tracee
.set_registers(pete::Registers {
rip: shellcode_address,
// shellcode会通过r9寄存器调用函数
r9: fn_address,
// 根据x86-64 ABI要求,将函数入参传递到寄存器中
rdi,
rsi,
// 根据x86-64 ABI要求,确保栈指针对齐到16字节
rsp: self.saved_registers.rsp & !0xf,
..self.saved_registers
})
函数fn_address是我们要调用的函数在目标进程中的虚拟地址,rdi和rsi是根据 x86-64 调用约定传递的前两个函数参数,rsp是栈指针,必须对齐到 16 字节以符合 ABI 要求。特别注意,fn_address必须是目标进程地址空间中的有效地址,否则会触发SIGSEGV信号导致进程崩溃。而目标进程的地址是不固定的,我们需要通过函数相对 so 文件的偏移量来计算。首先分别获取libc.so在 tracer 和 tracee 中的地址,可以通过/proc/<pid>/maps文件获取每个 so 映射到内存的地址。再根据函数在 tracer 中的地址计算函数在libc.so中的偏移量。最后在 tracee 中根据libc.so的地址与函数偏移量计算目标函数在 tracee 中的真实地址,即可根据该地址进行调用。
获取函数真实地址的代码比较冗长,感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仓库中的源码。
通过上述步骤,我们可以在 tracee 中调用dlopen函数,加载动态链接库,实现动态注入。
ptrace只是帮助我们实现了探针的动态注入,而真正的探针逻辑还需要我们自己实现。根据前文所述,借助ptrace可以让目标进程调用dlopen来加载动态链接库。而在动态库加载的过程中,会读取 ELF(Executable and Linkable Format) 文件中的.init_array段,该段中存放了一系列初始化函数的地址。C/C++编译器一般支持__attribute__((constructor))属性,可以将函数注册到.init_array段中。
__attribute__((constructor)) void my_init() {
// 初始化代码
}
而 Rust 中可以通过#[ctor]宏实现类似的功能:
#[ctor]
fn my_init() {
// 初始化代码
}
Probing 的注入框架不仅支持其内置探针模块,还支持用户自定义的探针库,提供了极高的扩展性。关于探针的具体设计细节,我们将在后续文章中深入探讨。
传统的 C/C++项目经常受 ABI(Application Binary Interface)兼容性的困扰。常见的 ABI 兼容性问题有两类:
- glibc 中函数的版本问题:为了保证 ABI 的兼容性,glibc 中的函数会有多个版本,比如
malloc函数就有malloc@GLIBC_2.2.5、malloc@GLIBC_2.3等多个版本。而动态链接库在链接时会在当前 glibc 中选取一个最新的版本,这就导致了在较新的系统下编译的 so 文件在较旧的系统上无法运行;
- C++的 ABI 问题:C++的 ABI 问题主要由于最近几年 C++标准的更新较快,导致 libstdc++库的 ABI 不断变化。其中最为常见的一种错误是
std::string类型在 C++11 标准中引入了短字符串优化(SSO)机制,导致std::string的内存布局发生了变化。而在 C++11 之前编译的 so 文件在 C++11 标准下运行时,会出现内存布局不一致的问题;
Probing 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解决 ABI 兼容性问题:纯静态链接与 zigbuild。
静态链接是解决 ABI 兼容性的一种经典方法,通过将所有依赖库代码打包到一个 so 文件中,并在链接阶段完成所有符号的解析,从而避免了运行时出现 ABI 问题。Rust 在构建 so 文件的时候默认使用纯静态链接,能够很大程度上避免 C/C++项目中的 ABI 兼容性问题。
Zig 是一种新兴的系统级编程语言,内置完整的交叉编译工具链,可针对不同 glibc 版本生成二进制文件:
zig cc main.c -o main -Dtarget=arch64-linux-gnu.2.31
这使得使用 Zig 工具链构建的 so 文件可以通过指定低版本的 glibc 来增加 so 文件的兼容性。
cargo-zigbuild是 Rust 构建工具cargo的一个扩展,可以在编译时指定 glibc 的版本,并借助 Zig 的工具链完成 so 文件的链接。
cargo zigbuild --target x86_64-unknown-linux-gnu.2.17
前文已经讨论了探针的动态注入与 ABI 兼容性问题,两者都尽最大的可能让 Probing 可以在任意环境下直接运行,而无须额外的配置。接下来我们将讨论 Probing 的打包发布问题,这是让 Probing 真正成为一个通用的工具的关键。
二进制工具发布通常有三种渠道:
- 发布源码:将源码发布到 github 等代码托管平台,用户可以自行编译;但往往构建一个复杂项目的环境是非常困难的,尤其是在分布式环境下;
- 发行版包管理器:将二进制工具打包成 rpm、deb 等包,发布到发行版的包管理器中,用户可以通过包管理器安装;但是不同发行版的包管理器不同,维护成本较高;并且同一个发行版的不同版本需要维护不同的包;
- pip/conda 等第三方发布平台:将二进制工具打包成 pip/conda 包,发布到第三方平台,用户可以通过 pip/conda 安装;但是这种方式往往需要用户安装额外的包管理器,不够方便;
不过对于 AI 领域的工具来说,Python 是必不可免的,因此基于 Python 包管理工具 pip 或者 conda 来发布 Probing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
不同于一般的 python 包,Probing 是一个以 Rust 为主要开发语言的工具,因此并不适合使用 setup.py 等传统方式来构建 python 包。这里我们选择直接使用脚本来打包whl:
def write_wheel_file(filename, contents):
with WheelFile(filename, "w") as wheel:
for member_info, member_source in contents.items():
...
return filename
def write_wheel(out_dir, *, name, version, tag, metadata, description, contents):
name_snake = name.replace("-", "_")
wheel_name = f"{name_snake}-{version}-{tag}.whl"
dist_info = f"{name_snake}-{version}.dist-info"
return write_wheel_file(
os.path.join(out_dir, wheel_name),
{
**contents,
f"{dist_info}/METADATA": make_message(...),
f"{dist_info}/WHEEL": make_message(...),
},
)
def write_probing_wheel(
out_dir, *, platform="manylinux_2_12_x86_64.manylinux2010_x86_64"
):
...
for name, path in {
"probing": "target/x86_64-unknown-linux-gnu/release/probing",
"libprobing.so": "target/x86_64-unknown-linux-gnu/release/libprobing.so",
}.items():
zip_info = ZipInfo(f"probing-{metadata["version"]}.data/scripts/{name}")
zip_info.external_attr = (stat.S_IFREG | 0o755) << 16
with open(path, "rb") as f:
contents[zip_info] = f.read()
...
return write_wheel(
out_dir,
name="probing",
version=metadata["version"],
tag=f"py3-none-{platform}",
metadata={...},
description=description,
contents=contents,
)
def main():
wheel_path = write_probing_wheel("dist/")
with open(wheel_path, "rb") as wheel:
print(f" {wheel_path}")
print(f" {hashlib.sha256(wheel.read()).hexdigest()}")
if __name__ == "__main__":
main()
该脚本主要使用wheel包中的WheelFile类来构建whl文件,并将构建出来的二进制写入到probing-{version}.data/scripts目录下。此外需要提供METADATA和WHEEL文件,分别用于描述包的元信息和 wheel 的版本信息。
本文主要讨论了 Probing 的核心机制——探针注入,并讨论了如何将这一机制变成一个通用工具,让其能使用到复杂多样的生产环境中,能够快速发布给尽可能多的用户。所有这些设计都是为了 Probing 的一个核心设计理念:解决问题时,应直接面对根本问题,避免陷入工具配置、环境搭建等元问题的循环中。或者可以认为这一设计理念是马斯克第一性原则的一种体现,缩短解决问题的路径,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。
在下一篇文章中将会介绍探针 so 的设计与实现。